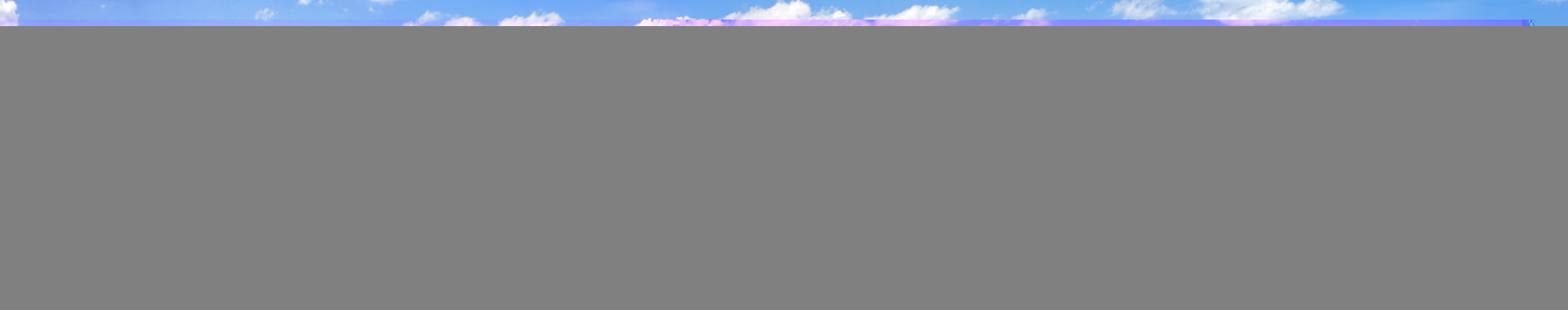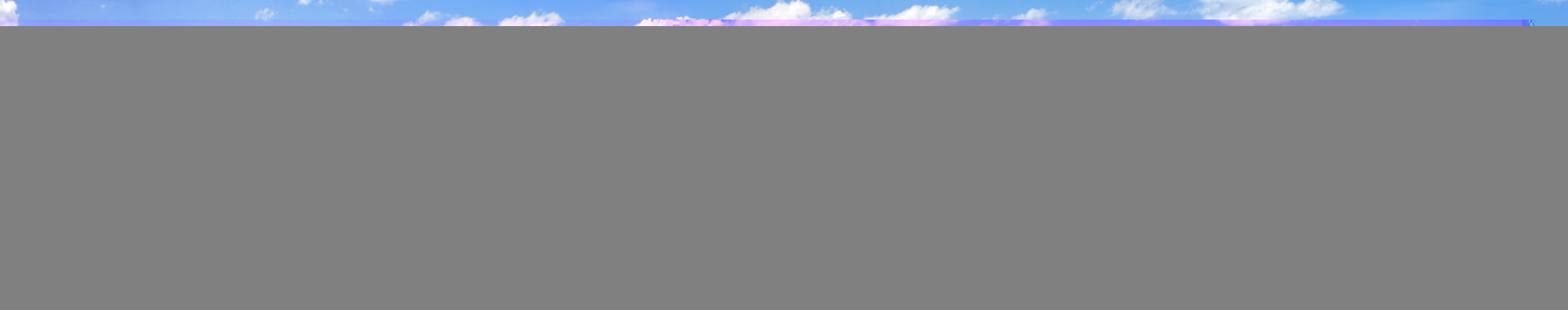2022年3月28日至4月18日,圍繞“一流本科專業暨本科課程”建設目标,英語系特别邀請Alberto Castelli(Alby)教授連續舉辦一系列導師領讀研讨沙龍活動。本系列領讀沙龍主要基于約翰•彌爾頓《失樂園》有關“知識欲望與人類救贖”這一主題内容展開,英語系師生一同研讀人文經典,探尋當代價值與啟示。本系列沙龍由白麗芳老師和王勇老師主持,英語系2020級、2021級部分同學、研究生及教師參加了整個領讀研讨活動。


領讀研讨活動伊始,Alby老師首先簡要介紹了《失樂園》作為文學作品的屬性特點。從英國内戰曆史背景出發,引出作者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所處的社會背景、政治宗教現實狀況以及個人經曆困境。回顧彌爾頓生平所遭遇的被捕、失明以及所經曆的失敗革命,呈現了其作為偉大詩人與革命文豪的恢弘人生境遇,提示其對惡魔之神滿懷同情的個人與社會曆史背景,描繪了其悲壯的政治情懷與人文關懷。對《失樂園》創作曆程的探尋,大緻可追溯至荷馬與《聖經》故事,激發有關惡魔之神撒旦與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一樣挑戰神權卻終而失敗的思考,也會聯想到蘇格拉底(Socrates)被判處死的命運。同時,如俄狄浦斯(Oedipus)一樣,《失樂園》裡的亞當也有對其身份的不斷尋找以及知識欲望(temptation of knowledge)的追尋探索,終有所獲。彌爾頓自己則猶如詩人但丁一樣,在《失樂園》中描繪勾勒了自己理想的宇宙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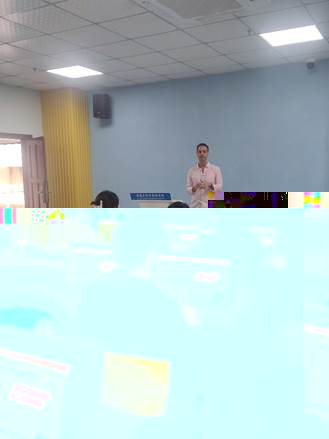
作為享譽西方文壇的偉大史詩,《失樂園》最初共10卷,後改變為12卷,每卷長達一千多行,具有鮮明獨特的英語語言風格與文體特征。總體上,《失樂園》以英語書寫,卻采用了拉丁語的表達結構,借用史詩的結構呈現悲劇主題,構成典型的悲劇史詩(tragic epic)。史詩以《創世紀》為故事原型,以彌爾頓自己作為叙述者推進深入思索,導向故事的主角撒旦,對神義論(Theodicy)進行追問,猶如正義女神狄刻(Dike)般不斷質問上帝“為何有惡魔存在?”“我們又因何而備受痛苦?”置身《失樂園》,彌爾頓表達了有罪的亞當遠勝過無罪的亞當,既有對夏娃試圖獨立于亞當而尋找自我身份過程的思考,也有對信仰與上帝是否異同的拷問。一方面,夏娃的激情與亞當的理性以及偷食禁果的勇氣與惡魔撒旦的理性誘惑有關,實際上也蘊含了亞當對夏娃的深沉摯愛。另一方面,勞動分工似乎成為人類“堕落”的開始,而撒旦以“邪惡與逃離”的理性勸誘,在《失樂園》中既彰顯了人類自身的雄心與傲慢,也影射了人類對知識的渴望與追求(a quest for knowledge)。在這個意義上,對身處21世紀知識爆炸時代的我們而言,智慧之樹(tree of knowledge)到底有何象征意義?重讀《失樂園》,看到的不僅是彌爾頓對“人類追求知識而受誘惑堕落”之偉大的肯定,還有對惡魔之神挑戰傳統與權威之勇氣的鼓勵。反觀當下我們所處的知識時代,《失樂園》中的“智慧之樹”很大程度上象征了“人類的限度”,我們人類生存中無所不在的限度。盡管成功需要不斷地突破各種限度,但同時也必須正視逾越限度而可能面臨的代價,對于未知的追尋與探索應該有一定的限度,而科技進步與革新當然更需要思考其可能的限度。




《失樂園》彰顯了愛情、知識、人性的複雜性。亞當和夏娃的愛情交織着權力與抗争、和諧與分裂;知識之樹雖令人垂涎卻是人類不得觸碰的禁區,知識樹上的蘋果帶給人類自我意識,也播下了沖突的種子;完美的背後滋生着不安,理性背後湧動着激情;人類渴望掙脫牽絆,又擔憂喪失安全;明明是内心怯懦、躲避責任,卻以愛情、誘惑、自由為借口,為自身尋求辯護……
《失樂園》開啟了人類的自我探尋之路,Alby老師的《失樂園》系列領讀沙龍也開啟了大家的經典閱讀之路。1658至1663年間,雙目失明、體弱多病的彌爾頓憑借内心的光亮,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失樂園》的創作,探尋人類關于“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根本問題;在21世紀的今天,當科學技術、人工智能滲透至人類生活的每個角落,人類更應該思考“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